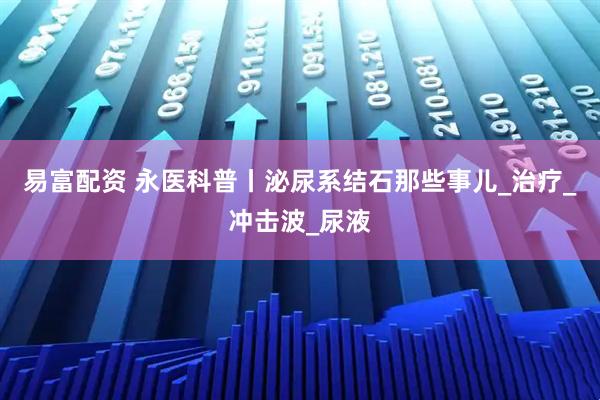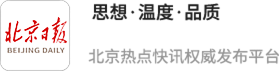吕文扬的指尖悬停在电子显微镜的调焦旋钮上德益配资,墨尔本凌晨三点的寂静被培养箱的低鸣打破。他的瞳孔里倒映着荧光标记的神经元图像——那些交织的绿色丝线,正在讲述阿尔茨海默症蛋白异常聚集的新线索,这是他读生物学博士的第二年,也是他在Walter and Eliza Hall研究所的第五十六次通宵实验,更是他转向计算生物学后的关键一战。
生物学博士课题的选定像一场宿命。本科在复旦研究植物基因编辑时德益配资,他总被导师说“太爱追问为什么”。这个习惯在澳洲彻底释放:他拆解实验数据时总要多问一层机制,连实验室的阿根廷博士后都感叹:“Lü的讨论像在拆俄罗斯套娃。”后来他干脆把分子动力学模拟和湿实验结合,用机器学习预测tau蛋白的错误折叠路径,意外登上了《自然-神经科学》的年轻学者专栏。
但吕文扬的实验室白大褂下,藏着个狂热的自然主义者。每个月的最后一个周末,他会驱车四百公里前往格兰屏国家公园,记录桉树林的生态变化。背包里永远装着三样东西:便携式基因测序仪、素描本(他坚持手绘能培养观察力),以及上海外婆寄来的薄荷糖。当同学们笑称他是“21世纪的达尔文”时,他反手群发了自己编写的物种识别APP——用公园采集的数据训练出的算法,现在连原住民护林员都在使用。
展开剩余37%2024年南极科考船招募越冬研究员时,这个怕冷的南方人第一时间递交了申请。面试官对他“用宏基因组学追踪极地微生物耐药性”的提案兴趣浓厚,但更惊讶于他随身携带的“小发明”:一个用3D打印零件组装的微型PCR仪。“极地的设备运输周期太长,”他眼睛发亮,“有些发现等不起。”
毕业答辩通过那天,吕文扬在实验室黑板上画了棵演化树。最末梢的分支标注着“吕氏选择”——下面潦草地写着:“在试管与旷野之间,做生命的翻译官。”此刻悉尼大学的教职offer静静躺在邮箱里德益配资,而他正给喜马拉雅旱獭保护区写着开源代码。
发布于:安徽省金鼎配资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